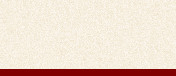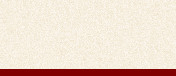|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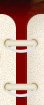 |
| ▌弘易連載:南懷謹 易經繫辭別講(十一) 達爾文的祖宗 |
弘易連載:南懷謹 易經繫辭別講(十一)
達爾文的祖宗
“方以類聚,物以群分,吉凶生矣。”人類文化最大的哲學問題出現了,關於這個方字,我們都曉得四四方方是方,方也可以代表空間的方位。但就文字學來說,講中國字要知道它的來源,方是怎麼來的呢?方是個像形字,像個猴子,這是簡單的象形。就像我們人,隨便這麼一畫,就像人了。所以方字就代表了猴子,或者是長的人,這就是本字的由來。後來簡用了,就給它改做四方的方;方方正正的方,是藉用來的。
我年輕時候看到一本《易經》的註解,也是受了近一百多年西方文化進來的影響,解釋這一段“方以類聚”,說方是代表細菌,人是細菌微生物變的,就是達爾文的思想,並以為人是由微生物慢慢變成猴子,猴子變成人類,所以猴子是我們的老祖宗。當時有位同學非常贊同這種說法,我說你們的祖宗是猴子變的,我的祖宗不是猴子變的,大家還拿了很多證據,辯論得一塌糊塗。
實際上,這句話是非常明白的。“方以類聚”包括了些什麼呢?譬如拿政治來講,就包括了地緣政治、地理環境等等的關係。像我們這個地球,乃至任何一個地方,東南西北方位不同,那個地方生長的物類,以及人的形態個性也都不相同。平常我們看到一個陌生人,一看便知道他是北方人、南方人或者東方人,大概判斷得八九不離十。不像你們在寶島溫室中長大的人,沒有這種經驗。
由於每一個地方的不同,生長的植物、動物都有差異。新竹以北的壁虎不會叫,新竹以南的壁虎會叫,這就是所謂的“方以類聚”,類就是所謂的歸類白彰化人、嘉義人都不同,有些植物也是一樣。像阿里山種的香蕉,我只要拿來⋯看,就知道是阿里山的,尤其吃到嘴裡,一下就分別出來了。日本的蘋果與韓國的完全不同,這就是“方以類聚”。所以西方人是西方人,東方人是東方人,由於地區不同,所生長的人物,乃至萬物都不相同。
“物以群分”的這個物,指的是籠統的物,不定的物,一層一層的分類,一種一種的分類。這是自然的現象。雖然說“方以類聚,物以群分”,是一種自然的現象意識,但這裡邊就有好有壞了。所以我常常講,台灣有些人鬧台獨的問題、分離的問題,這不稀奇。一點都不稀奇。中國人“方以類聚,物以群分”已經鬧了幾千年。
清兵人關,有明、清之爭;後來國民革命後,又有南北之爭,可以說從一九二四年以來,都是南北之爭。再後來革命黨內部又有不同派別之爭⋯⋯一路的到底,反正是“方以類聚,物以群分”!人類只要有空間、有時間,人類只要存在、只要有社會就有紛爭。
大家注意“社會''這兩個字,我們當年一般不叫社會學,而叫群學。當時有一本很有名的著作,是嚴復翻譯的,叫《群學肄言》,就是社會學。到現在《群學肄言》的價值還很高,他用中國的文字,比較接近新舊之間的文學技巧來翻譯,現在重新拿出來看看,它的社會思想的價值還是很高、還是存在的,而且,比現在人白話翻譯的還要好。
“物以群分”,就是說形成社會物類的不同寺於是“吉凶生矣”,有人類就有意見,就有問題。因不同意見而相爭,這是沒有辦法的事。所以讀了《易經》以後來看天下事,看天下的治亂紛爭,就知道那是人力很難挽救的事實。“方以類聚,物以群分,吉凶生矣!”這裡從陰陽剛柔、天地宇宙講到物理世界,講到物質世界;講到物理世界與物質世界空間關係;然後講到“方以類聚”這個地球、人群物理的關係;因為人類有“物以群分”,就有意見,有意見便要爭,爭就有吉有凶。所以吉與兇就是類聚群分,群體社會出現後的必然結果。
|
|
|
 |